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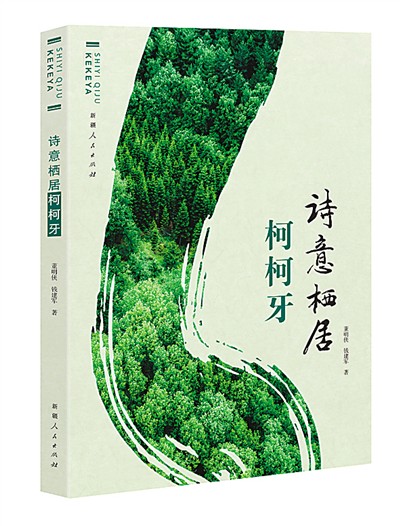
新疆壮美明丽,作为一个新疆人,我愿纵马驰骋于天山南北的每一个角落,但也许不包括柯柯牙。为什么?在我遥远的记忆里,那是一片亘古的荒原、宁静的死水。柯柯牙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,是阿克苏市风沙的策源地,那里寸草不生、盐碱板结、风沙肆虐,每年有近100天,人们的生活被沙尘笼罩。现在,柯柯牙变了。得益于柯柯牙绿化工程这一全国荒漠绿化的典范工程,这里成了边疆碧野、瓜果之乡。
毋庸置疑,这是阿克苏人克服天灾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举。董明侠、钱建军二人集三年之力完成的报告文学《诗意栖居柯柯牙》,则是对这个壮举的忠实记录。
作者笔下,这样一幅画卷徐徐展开:阿克苏人民面对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横亘百万余年的荒原戈壁,数代人接力,在茫茫黄沙间构筑起一条逾百万亩的人工林带。我看到一个个身影、一张张面庞。他们毫不吝惜地在贫瘠的土地上重重砸下沉甸甸的汗珠,前前后后30年,无数柯柯牙人奉献出这珍贵的“一点水”,竟孕育了柯柯牙的“绿色长城”。只此青绿,正当春归,柯柯牙精神由汗水凝聚而生。
1985年,时任阿克苏地委书记的颉富平感到,如果不根治风沙,就不能改善阿克苏人民的生活,更无法把这个随时有覆巢之虞的阿克苏城传给子孙后代。于是,地委班子当年就发动全社会力量,包括各族干部群众和驻地官兵,人工治沙、造林绿化。自此,柯柯牙绿化工程正式拉开帷幕,30年里,七任地方领导更迭,绿化工程一直坚持下来,共组织54次大会战,植树造林115.3万亩、累计栽植树木1337万株。
我们回到最初的原点,柯柯牙绿化工程是一个“三无”工程,没有项目、没有资金、没有设备,但为何阿克苏人能有此壮举?
还是从书中找答案。黄风漫卷,黑云压城,阿克苏人民的生存其实一直在危机中。在这样的生态下,人的精神状态是麻木的。面对千百年来酷烈无情的荒漠,人们已经漠然,只能无言承受。然而,当一个新来的书记带着善念,想要为这里的人们改变点什么的时候,人们最简单朴素的渴望突然就被点燃了。首先是取得领导班子的集体认可,其次迅速获得广大军民群众的支持响应,这才有了阿克苏沙海上浩浩荡荡几十年的精耕细作。反过来说,恶劣的环境使人心变得粗糙厚钝,所以治理环境不仅是物质上的,也是在恢复人心灵中隐藏在麻木背后的那点灵动和敏锐。
我非常理解本书的结构框架,生存、发展、生态是具有递进关系的。我们有生存权,也有发展权;有经济权,也有环境权;有“利权”,也有“美权”。其实,当我们对环境不满足,当我们要将自己从生活的粗粝和艰苦中解放出来时,我们也是在追求一种纯粹的美。如果没有这点美,正常的道德秩序和心灵律令将遭到严重损害,而且我们文明的正当性会受到质疑。
人类发展史,可以被解读为对自然深度介入的历史。阿克苏人介入自然,是要自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,但植树造林本身,不是侵入型介入,而是融合式介入,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寻求新的融合。可以说,是阿克苏人成就了今天的阿克苏,糖心苹果、红枣、核桃,无一不是自然的馈赠;是大风大雨和连畦的流水、成排的树荫,见证了今天的柯柯牙精神。
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,是“诗意栖居”四个字。它意味着,绿化工程不仅是阿克苏人的生态治理任务,更指向一种家园意识——人们审美化地栖居于自然之中。比如,护林员勇敢阻拦偷苗和伐树行为,难道他仅仅出于职业操守吗?可能更因为不忍心看着才扎根的小树就这样失去了成长机会。任何一个人,都会很自然地把美当作环境伦理的一个尺度。生命是美的,而保护生命之美的行为则是善的。这和人们需要从自然中获取庇护的要求一样,都是人性对于基本善的演绎。
《礼记·礼运》说:“人者,天地之心也,五行之端也。”这反映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,人在自然中的价值凸显必须是一种超越性的、统摄性的。人和自然关于利用与治理的纠葛,源头问题是忘记了人类与自然的多维关系。孤立的价值主体在经验中是不存在的,冷漠的自然客体其实也只是现代思维中假设出来的,人只有与自己身处的外部环境建立了合理的关系系统,才能在人化自然中做到美善合一。在此前提下,经济利益只是生态治理的副产品,它永远不是治理的核心目标和唯一价值。
我们要的是“乐”,乐山乐水的怡然之乐。书中勾勒了阿克苏农家乐的历史,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象征,农家乐建立在经济果林中,利用自然做着服务人心灵的工作,更重要的是,农家乐还创造了就业,给无家可归者提供了家的温暖。这一文学呈现,把审美体验和生命感悟一并纳入生态治理所关注的视野中。如此,自然就变得有情而多情起来。自然的美是自洽的,不需要文字来赋予。因此,柯柯牙精神就不仅是奋斗精神,还有奉献精神,这背后不仅仅有对基本善的追求,还有对自洽美的坚守。(作者:邱华栋 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)